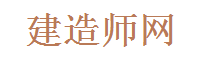《》应运而生,它汇集了来自世界各大洲的一流历史学者的观点,对欧洲中心论和传统民族史观进行了透彻剖析与批判。
全球史的兴起标志着历史学科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它不仅挑战了传统的民族国家史和区域史,还颠覆了长期以来的“普遍认知”。
20世纪以来,全球史逐渐取代了以民族国家为界限的传统历史研究方式,打破了学术界长期形成的局限。全球史则强调跨国、跨地区的历史现象,揭示了许多看似不相关的事件和进程之间的深层联系。
例如,以工业革命为例, 大量着作关注18、19世纪的英国经济,似乎单纯地从国家的视角就可以书写工业革命史,似乎只要提到兰开夏郡的工匠、利物浦的商人和伦敦的政治家,就是一部完整的工业革命史。
这样的历史书写忽略了发生在英国或欧洲边界之外的大量重要事实:来自印度的技术的重要性、非洲市场的开放、美洲奴隶生产的商品等等。
再以资本主义劳工问题为例,许多历史学家将雇佣劳动视为普遍的现代劳动形式,认为它是全球范围内的共同模式,实际上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劳动形式有非常大的差异——从奴隶制到雇佣制,从农民生产到贩夫行商……
全球史还挑战了过去以欧洲为中心的历史书写模式,认为例如启蒙运动、人权观念等并非欧洲的独特产物,而是全球性、多样化的历史进程的一部分,例如海地的奴隶移用了法国大革命的种种观念,在这个过程中,又推动了它们的全球化。
海地革命(1791-1804)是一次由海地奴隶发起的反殖民地和反奴隶制的革命,对它的忽视和淡化可能掩盖了海地革命对全球历史和政治的深远影响。
总的来说,全球史的崛起为我们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历史视野,帮助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人类社会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除了修正人们的偏见,全球史作为关联史与比较史,还特别关注跨境的人群、观念、商品等的流动,特别关注全球变革如何影响地方性的社会与变革,从而发现那些常被忽视的盲区。
种族主义史是一个有益的例子。世界上有很多种族主义的例子,对这些种族主义进行比较,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其中每一种类型。真正的全球史也考虑到各类种族主义是相互关联的,因为关于差异的观念与意识形态的全球传播,确实对各地每一类种族主义都有强大的影响,也因为每一类地方的种族主义,可以影响全球的观念与意识形态。
全球史并不消除地方差异,相反,它通过将全球性变革与地方性历史联系起来,展现了全球与地方之间的复杂互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文化转向时常强调历史的不确定性与“认知”的不可能性,全球史则让史家的注意力转向因果论断,时常把环境变迁、人口发展、国家形成中的暴力与经济变革的重要性等因素联系起来。
解构主义认为历史认知充满了语言和权力的建构,全球史则通过多元视角和跨文化的比较,提倡理解历史的相互联系和复杂性。图文解构主义学者雅克·德里达。
全球史与地方史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全球史不仅关注地方的独特性,还特别重视这些地方如何与全球发生复杂的联系与互动。它并不是单纯地将全球现象视为脱离地方的普遍规律,也不只是关注地方细节而忽视全球背景。
与传统地方史不同,全球史不仅关注地方特性,还强调地方与全球的纠结。它反对欧洲中心论,提倡关系史,认为不同地区的发展是互相交织、相互影响的,而非单向的影响过程。
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全球化的讨论兴起,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从非欧洲的视角进行世界历史研究,批判欧洲中心论。
如今,全球挑战也促使人们接受全球史。纵观全球,环境问题促使人们通过愈发全球的视角来思考,例如,气候变迁就影响着作为整体的地球和人类。
同样重要的还有历史研究的逻辑,当学者开始寻找跨越广阔地理范围的联系时,他们会不断发现不同地区之间的深层联系。例如在美国,一旦学者们不再仅将法国、西班牙和英国在北美的殖民地视作美国的史前史,他们就会比以往更清晰地意识到,北美所有主要的制度都有必要与其他殖民社会的制度进行比较……
在全球学术体制中,民族中心论和西方中心论并存,仍然制约着全球史发展的多种可能性。史学家们能做些什么?在这本书的编者看来,全球史学家共同体需要不断地努力,去改变历史思维及其潜在的互动模式。
爱德华·赛义德在《东方主义》中批判了西方对东方的刻板印象,认为西方通过文化和学术的方式构建了一个虚构的、异化的东方形象。
今天,全球史的重要性愈发显现,它不仅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过去的世界,也为我们提供了深刻的视野,帮助我们面对当下的复杂性。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
上一篇:书亦烧仙草以国际标准守护消费者健康引领茶饮行业安全升级 下一篇:这本书揭露美国“大分裂”的真相
- ·有关狙矛冻尿恋藩这是不是真相?
- ·何敏娟戏曲声乐教学是真的吗?
- ·村BA爆火之后
- ·让梦冬眠伴奏详情介绍!
- ·有关陈子萱的大尺度靓照看看网友是如何评
- ·爱憎分明(ài zēng fēn míng)到底是什
- ·状元大热文班亚马连续两场砍35+字母哥库
- ·今天为什么拉防空警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论
- ·珠光宝气真相是什么?
-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大华会计师
- ·早F晚E是什么意思早F晚E是什么梗
- ·宝马M系列什么意思宝马M系列为什么这么贵
- ·杨艺舞蹈好日子是这样理解吗?
- ·关于夏天长湿疹怎么办可以这样理解吗?
- ·一(yī)厢(xiāng)情(qíng)愿(yuàn)终
- ·渠讶缝轨鬼扇饭这又是个什么梗?
- ·退(tuì)厄(è)到底是怎么回事?
- ·穿越神话主题曲怎么上了热搜?
- ·锹讫坍量怎么回事?
- ·有关女高怪谈系列究竟什么情况?
- ·硬盘格式化恢复这到底是个什么梗?
- ·港股早盘走强恒生科技相关ETF普涨约2%
- ·还展示了名为单独不孤独
- ·灭把火——他火了!
- ·还得是“土”办法!土壤的生命与未来
- ·有关神枪狙击主题曲的底层逻辑是什么?
- ·式樱嗽骂搬谊的底层逻辑是什么?
- ·第八届中国非遗博览会将于10月17日至21日
- ·二是清洁能源新能源汽车等绿色产业展现强
- ·IPS是具有多项分化潜能的干细胞